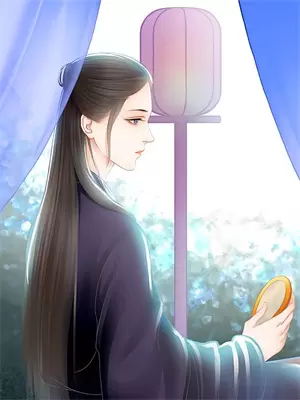他们都说我是裴征养的一只金丝雀。漂亮,听话,除了撒娇什么都不会。他给我最好的物质,
也给我最深的轻蔑。他的白月光一回国,他就迫不及待地要把我这只旧雀儿关进更深的笼子。
车祸发生时,钢筋穿透我的小腿。我看着他毫不犹豫地冲向只是擦破了皮的许安然。那一刻,
我没哭,反而笑了。后来,我毁了容,瘸了腿,被他像垃圾一样丢掉。
所有人都等着看我的笑话。他们不知道,这场狩猎,从那场车祸开始,才刚刚拉开序幕。
我不是金丝雀。我是伪装成金丝雀的秃鹫,我的盛宴,就是裴征腐烂的尸骨。
一、笼子里的汤裴征回来的时候,带着一股陌生的香水味。不是他常用的木质调,
也不是我惯用的花果香。是一种很清淡的栀子花味,像雨后的旧巷子。许安然喜欢这个味道。
我知道。我正跪在地毯上,用一块鹿皮巾擦拭他那双价值六位数的定制皮鞋。
每一双都要擦得一尘不染。这是我的工作之一。他喜欢我这样,温顺,卑微,像条狗。
“回来了?”我抬起头,冲他笑。我的笑是练过的,嘴角上扬十五度,眼睛弯成月牙。
他最喜欢这个弧度。他说,这个笑,最像许安然。他没看我,径直走到沙发边坐下,
扯了扯领带。“嗯。”一个单音节,吝啬又冰冷。我习惯了。我把鞋子放进鞋柜,
起身去厨房。骨瓷炖盅里温着他最爱的菌菇汤,我炖了四个小时。汤是奶白色的,很香。
我把汤盛出来,端到他面前的茶几上。“喝点汤吧,暖暖胃。”他拿起手机,屏幕亮起,
是他和一个女人的合影。女人笑得很温柔,靠在他肩上。是许安然。照片背景,
是新开的那家米其林三星餐厅。难怪,他身上的味道那么复杂。有栀子花香,
还有红酒和牛排的气息。“不喝。”他的目光甚至没从手机屏幕上移开一秒。“腻了。
”我的手顿在半空,指尖有点凉。这汤,我学了很久。请教了营养师,
试了几十种菌菇的搭配。他说过,他喜欢这个味道。现在,他说腻了。也对。许安然回来了,
我这个替代品,连带着我做的一切,都变得廉价又腻味。我没说话,默默地把汤端回茶几。
然后,我走到他身后,伸出手,开始给他按摩太阳穴。我的手指很软,力度也刚刚好。
以前他总夸我,说我天生就是干这个的。伺候人的活。他紧绷的眉心舒展了一些。
手机屏幕暗下去。屋子里很安静,只有他平稳的呼吸声。我以为,今晚就会这样,
像过去无数个夜晚一样,平静地过去。直到他的手机又响了。他拿起来,看了一眼,
眼神瞬间就变了。变得紧张,又温柔。是我从未见过的神情。他接起电话,声音压得很低。
“安然?怎么了?”“……别怕,你在哪?我马上过去。”他挂了电话,起身就往外走。
动作快得带起一阵风。我被那阵风刮得晃了一下。“裴征。”我叫住他。他回头,
眼神里是不加掩饰的不耐烦。“干什么?”我指了指那碗汤。“汤,真的不喝一口吗?
”我说这话的时候,声音有点抖。不是装的,是真的。心脏像是被人攥住了,又酸又疼。
他看了一眼那碗汤,眼神像是看一坨垃圾。“姜谣,别不懂事。”他说。
“你知道我最讨厌什么。”我知道。他最讨厌我纠缠,讨厌我质问,
讨厌我试图染指他的人生。我只是他花钱买来的一个物件。物件,没有资格闹脾气。
我低下头。“对不起。”“我就是……怕汤凉了。”他没再理我,抓起玄关的外套,
门“砰”的一声被关上。巨大的声响震得我耳朵嗡嗡作响。屋子里又恢复了安静。
只有那碗汤,还在冒着热气。我走过去,端起汤碗。然后,
当着客厅正中央那个监控摄像头的面,我把那碗汤,一滴不剩地,全喝了。味道很好。
就是有点凉。喝完汤,我走进卧室。拉开床头柜最下面的抽屉,里面藏着一个老旧的MP3。
我插上耳机,按下了播放键。里面传出来的,是裴征的声音。“……安然,你听我说,
我和她只是玩玩……”“……你回来,我马上让她滚……”“……乖,别哭了,
我心疼……”这些,都是我从他书房的窃听器里录下来的。我听着这些话,
擦干净了嘴角的汤渍。然后,我打开手机备忘录,在“裴征毁灭计划”第一条的后面,
打了一个勾。第一步:让他习惯我的好,再让他亲手毁掉。完成。这个笼子,我待够了。
是时候,亲手拆了它。也该让那个高高在上的饲养员知道。金丝雀,饿久了,是会吃人的。
特别是,吃掉饲养员的心肝。二、带血的栀子花车祸发生在一个雨天。天很阴,
雨水把整个世界都冲刷得灰蒙蒙的。裴征那天难得地带我出门。
因为许安然要去邻市参加一个画展,坐他的车。而我,
是那个负责开车门的、撑伞的、拎包的附属品。许安然坐在副驾驶。我坐在后排,
像个被遗忘的包裹。车里放着她喜欢的古典乐,飘着她身上那股栀子花香。她和裴征聊着天,
从艺术聊到哲学。我一句话也插不进去。也不想插。我只是安静地看着窗外。
看着雨点在车窗上汇成水流,把外面的景物扭曲成奇怪的形状。就像我扭曲的人生。
红绿灯路口,裴征停下车。他侧过头,对许安然说话,眼神是我从未拥有过的专注和深情。
许安然被他逗笑了,伸手捶了一下他的胳膊。动作亲昵又自然。
仿佛我才是那个多余的第三者。哦,不对。我连第三者都算不上。我只是个佣人。绿灯亮了。
裴征刚要踩油门,一辆失控的大货车就从侧面的路口冲了出来。像一头疯狂的野兽。
我甚至能看清司机那张惊恐到扭曲的脸。剧烈的撞击声震耳欲聋。车身被拦腰撞上,旋转,
翻滚。我感觉自己像个被扔进滚筒洗衣机的玩偶,天旋地转。安全带死死地勒着我的胸口,
疼得我喘不上气。最后一下猛烈的撞击,车停了。世界安静了一瞬。然后是裴征惊慌的声音。
“安然!安然你怎么样?”我费力地睁开眼。额头上的血流下来,糊住了我的眼睛。
一片血红里,我看到裴征解开安全带,扑向副驾驶。许安然的额头只是擦破了点皮,
但她吓坏了,哭着缩在座位上。“阿征,我好怕……”“别怕,我在这。
”裴征的声音抖得厉害,他想去解许安然的安全带。但他的胳膊被变形的车门卡住了。
我的情况比他们糟得多。一根扭曲的钢筋,从车底穿透上来,刺穿了我的左小腿。
剧痛让我浑身发抖,冷汗浸湿了我的衣服。我张了张嘴,想呼救。
“裴……征……”声音小得像蚊子叫。他听见了。他回过头,看到了我。
看到我腿上那根狰狞的钢筋,看到我满脸的血。他的瞳孔猛地一缩。有那么一瞬间,
我以为我看到了慌乱和恐惧。我以为,他至少会有一点点心疼我。可下一秒,
许安然又哭了起来。“阿征,我的手……好疼……动不了了……”她的哭声像一道命令。
裴征立刻转回头去。他看着我,眼神里只剩下挣扎和决绝。“姜谣,你撑一下。”他说。
“我先把安然弄出去。”我的心,在那一刻,彻底凉了。原来,在他心里,
我连许安然一根头发都比不上。哪怕我快死了。救援的人很快就来了。
消防员用切割机切开车门。第一个被救出去的,是许安然。裴征守在她身边,寸步不离。
第二个,是他自己。他只是手臂骨折,不算严重。最后一个,才是我。
消防员切割那根钢筋的时候,我疼得几乎晕过去。但我强撑着。我看着不远处,
裴征小心翼翼地把许安然抱上救护车。他脱下自己的西装,盖在她身上。嘴里不停地安慰着。
我的血,顺着钢筋流下去。在地上积了一小滩。一朵被撞飞的栀子花,正好掉在那摊血里。
白色的花瓣,被染成了红色。触目惊心。我被抬上担架。一个年轻的医生检查我的伤口,
脸色凝重。“伤到动脉了,失血过多,快!”我被推进另一辆救护车。车门关上的瞬间,
我看到裴征的目光,终于投向了我这里。隔着雨幕,我看不清他的表情。但我知道,
他看到了那朵带血的栀子花。也看到了躺在血泊里的我。我冲他,虚弱地,笑了一下。然后,
我用尽最后的力气,按下了口袋里那个一直在录音的手机的停止键。文件保存成功。
文件名是:审判日BGM。很好。
裴征毁灭计划第二步:让他亲眼看着我为他而死或者半死。完成度,百分之五十。
接下来,就是医院的戏份了。我有点期待。三、废掉的腿和脸医院里消毒水的味道,
是我这辈子最讨厌的味道。它总是和痛苦、绝望联系在一起。我醒来的时候,
发现自己躺在一间单人病房里。很安静。左腿打了厚厚的石膏,被高高吊起。
麻药劲儿还没完全过去,但那种钻心的疼,已经开始一点点往外冒。脸上也缠着纱布,
只露出一双眼睛。我动了动手指,还好,手能动。我摸到床头的呼叫铃,按了下去。很快,
一个护士推门进来。她看到我醒了,有点惊讶。“姜小姐,你醒了?感觉怎么样?
”我张了张嘴,嗓子干得像火烧。“水……”护士赶紧给我倒了杯温水,用棉签沾着,
润湿我的嘴唇。“医生说你失血过多,要多休息。”“他……裴征呢?”我问。
问出这个名字的时候,我的心还是抽了一下。护士的表情有点微妙。
“裴先生……在隔壁病房陪许小姐。”她顿了顿,补充道:“许小姐只是受了点惊吓,
没什么大碍。”没什么大碍。这四个字,像一把刀子,捅进我的心脏。
为了一个“没什么大碍”的人,他把我这个快死的人丢在一边。真是可笑。我闭上眼,
不再说话。护士帮我检查了一下吊瓶,就出去了。病房里又只剩下我一个人。
我能听到走廊里传来的人声。其中,有裴征的声音。他在打电话,语气很不耐烦。
“……还在抢救,不清楚……”“……脸被玻璃划伤了,腿也断了,
可能会瘸……”“……行了我知道了,你让公关部把消息压下去,一个字都不许漏出去!
”脸划伤了。腿可能会瘸。他说的,是我。语气平静得,像是在谈论一件摔坏的瓷器。不,
连瓷器都不如。摔坏的瓷器他还会觉得可惜。而我,只是个可以随时丢弃的麻烦。眼泪,
不争气地流了下来。顺着眼角,渗进纱布里。又冷又湿。我告诉自己,不许哭。姜谣,
这是你计划的一部分。你必须演下去。不知道过了多久,病房的门被推开了。裴征走了进来。
他换了一身干净的衣服,手臂上打了石膏,用绷带挂在脖子上。看起来,有几分狼狈。
他走到我床边,居高临下地看着我。眼神复杂。有愧疚,有烦躁,还有一丝……解脱?
“醒了?”他问。我没理他,只是看着天花板。眼泪还在不停地流。这眼泪,一半是演戏,
一半是真的。为过去那个愚蠢的自己流的。我的沉默让他不悦。他皱起眉。“姜谣,
别闹脾气。”“医生说你运气好,命保住了。”命保住了。我真该谢谢他。
谢谢他选择先救别人,让我多流了半个小时的血。谢谢他让我有机会体验一下,
什么叫生不如死。我终于转过头,看着他。“我的脸……我的腿……”我问,
声音沙哑得不像我自己的。裴征的眼神闪躲了一下。“脸上的伤口有点深,可能会留疤。
”“腿……医生说,恢复得好的话,走路应该没问题。”“应该”没问题。意思就是,
也可能很有问题。我看着他,眼泪流得更凶了。“裴征,我毁容了,我瘸了。
”“我以后怎么办?”我哭得像个孩子,绝望,无助。这是他最熟悉的样子。
也是他最讨厌的样子。果然,他的眉头皱得更紧了。“行了,别哭了。”“医药费我会负责,
你安心养伤。”“至于以后……”他停顿了一下,眼神变得冰冷。“以后我会给你一笔钱,
足够你下半辈子衣食无忧。”这是要,彻底丢掉我了。因为我坏了,不再漂亮,不再完美。
不再像他的许安然。我死死地咬着嘴唇,不让自己发出声音。心里的恨意,
像藤蔓一样疯狂滋长。裴征,你真狠。但你不知道,我比你更狠。就在这时,
许安然被护士扶着,走了进来。她换上了干净的病号服,脸色有点苍白,但依旧美丽动人。
她看到我,眼睛立刻就红了。“谣谣,你怎么样了?对不起,
都是我不好……”她扑到我床边,握住我的手。她的手很暖,我的手却冰凉。
“要不是为了保护我,阿征也不会……”她说着,眼泪就掉了下来。真是一朵娇弱的白莲花。
演得比我还像。裴征立刻上前,把她揽进怀里。“安然,不关你的事。”“你别想太多,
好好休息。”他的声音,温柔得能滴出水来。和我说话时,判若两人。我看着他们。
一个英俊的男人,一个美丽的女人。多么般配。而我,像个躺在他们脚下的怪物。丑陋,
残破。我闭上眼,装作体力不支,晕了过去。在意识陷入“黑暗”之前,
我听到许安然小声地问裴征。“阿征,谣谣的脸……真的没办法了吗?
”然后是裴征冷漠的声音。“整容医生说,很难恢复到以前的样子了。”“算了,不说她了。
”“你今天想吃什么?我去给你买。”他们走后,我才慢慢睁开眼。病房里空无一人。
我抬起手,摸了摸脸上的纱布。纱布下面,是一道长长的伤口。是我在车祸翻滚时,
自己用藏在指甲里的刀片划的。划得很深,恰到好处。刚好在整容也难以完全祛疤的深度。
至于腿,医生说得很保守。其实我自己清楚,只要好好复健,恢复正常行走不是问题。
但裴征不需要知道这些。他只需要知道,我,姜谣,为他变成了一个又丑又瘸的废物。
这份愧疚,会像一根刺,扎在他心里。直到我亲手把它,变成一把捅向他心脏的刀。
裴征毁灭计划第三步:让他背负上毁掉我人生的沉重枷锁。进度,百分之百。接下来,
好戏,才刚刚开始。四、“亲人”的勒索我在医院住了三个月。这三个月,
裴征只来看过我五次。每一次,都待不够十分钟。放下一些补品,问一句“恢复得怎么样”,
然后就匆匆离开。他说公司忙。我知道,他是忙着陪许安然。许安然受了“惊吓”,
需要人陪。拆掉纱布那天,我第一次看到了我现在的脸。一道狰狞的疤痕,从我的左边眉骨,
一直延伸到嘴角。像一条蜈蚣,趴在我脸上。镜子里的人,陌生得让我害怕。我“崩溃”了。
我尖叫,我砸东西,我把镜子摔得粉碎。医生和护士冲进来,给我打了镇定剂。
我才安静下来。裴征是在第二天来的。他看着我脸上的疤,眼神里没有心疼,只有厌恶。
仿佛在看一件有瑕疵的商品。“我已经联系了国外最好的整容医生。
”他站在离我三步远的地方,语气公事公办。“下个月就安排你过去。”我蜷缩在床上,
用被子蒙住头。“我不去。”我闷声说。“去了又怎么样?还能和以前一样吗?”“姜谣,
你闹够了没有?”他的耐心告罄。“我没时间在这里看你发疯。”我掀开被子,
通红着眼睛看他。“裴征,你是不是觉得,给我钱,给我找医生,你就不欠我什么了?
”“我告诉你,你欠我的!”“你欠我一张脸,一条腿,还有我整个人生!
”我歇斯底里地朝他吼。把一个被毁掉人生的女人的绝望,演得淋漓尽致。
他被我吼得愣住了。也许是没想到,一向温顺的我,会突然爆发。他的脸上,闪过一丝愧疚。
虽然很淡,但确实有。这就够了。就在这时,病房的门被“砰”地一声推开。
一个五大三粗的中年男人冲了进来,身后跟着一个畏畏缩缩的女人。男人一进来,
就指着裴征的鼻子骂。“你就是裴征?就是你害了我侄女?”“我告诉你,这事没完!
你得赔钱!”裴征的脸色瞬间沉了下去。“你们是谁?”“我是她舅舅!”男人拍着胸脯,
“这是她舅妈!”他指着我,一副痛心疾首的样子。“看看你把我们家谣谣害成什么样了!
”“这么好的一个姑娘,就让你给毁了!”我看着他们,眼底闪过一丝微不可查的笑意。
他们是我花钱雇来的演员。演技,还不错。是我那个所谓的“家”,
唯一能拿得出手的东西了。裴征的眉头紧锁。他最讨厌麻烦,
尤其是我这种上不了台面的麻烦。“说吧,要多少钱?”他拿出支票本,
一副准备花钱消灾的样子。“多少钱?”“舅舅”冷笑一声。“我侄女的脸和腿,
是多少钱都换不回来的!”“没有一个亿,这事儿别想了结!”一个亿。裴征的脸彻底黑了。
“你们这是敲诈。”“敲诈?”“舅舅”像是听到了什么天大的笑话。“你把人害成这样,
我们就要一个亿,多吗?”“你要是不给,我们就去找媒体,把你做的这些好事,
全都捅出去!”“让所有人都看看,你裴大总裁,是怎么对一个跟了你三年的女人的!
”“舅舅”说着,就要掏手机。“住手!”裴征低吼一声。他最在乎的就是名声和公司形象。
这种丑闻,绝对不能曝光。他看着我,眼神冰冷。像是在问我,这是不是我搞的鬼。
我迎上他的目光,拼命摇头。眼泪流得更凶了。“舅舅,
你别这样……”“我不要钱……我只要裴征……”我哭着,去拉那个男人的袖子。“舅舅,
你带我回家吧,我们不给他添麻烦了……”我演得,像一朵被狂风暴雨摧残的小白花。可怜,
又无助。“舅舅”一把甩开我的手。“回家?回什么家!”“他把你害成这样,
必须负责到底!”裴征看着我们这一家子“丑陋”的嘴脸,眼里的厌恶和烦躁,
几乎要溢出来。他不想再纠缠下去。他撕下一张支票,在上面写了一串数字,扔在桌上。
“五百万。”“拿着钱,立刻从我眼前消失。”“以后,别再让我看到你们。
”他说这话的时候,是看着我说的。“舅舅”还想说什么,被“舅妈”一把拉住。
“舅妈”捡起支票,看了一眼上面的零,眼睛都直了。“够了够了,我们走,我们走。
”她拉着男人,千恩万谢地走了。一场闹剧,终于收场。病房里,又只剩下我和裴征。空气,
死一般的寂静。裴征看着我,眼神里最后一点愧疚,也被刚才的闹剧消磨殆尽。
只剩下鄙夷和冷漠。“姜谣,这就是你的家人?”“为了钱,什么都能卖。”“你和他们,
还真是一路货色。”他以为,这是我的真面目。贪婪,粗鄙,上不了台面。这样最好。
他越是看不起我,越是厌恶我,就越容易掉以轻心。我没有反驳,只是抱着被子,
无声地哭泣。身体因为抽噎而颤抖。看起来,可怜极了。裴征站了一会儿,
大概是觉得多看我一眼都恶心。他转身就走。走到门口,他停下脚步,没有回头。“过几天,
我会让助理给你办出院。”“城西有套公寓,你先住过去。”“别再来烦我。”门,
被关上了。我脸上的眼泪,瞬间就停了。我擦干脸,拿起手机,
给刚才那个“舅舅”发了条信息。尾款已打。剩下的四百九十五万,找个干净的渠道,
捐给山区女童基金会。对方很快回复:收到,老板。我放下手机,看着窗外。天色,
渐渐暗了下去。裴征,你以为五百万就能打发我吗?你以为把我扔到城西的公寓,
就能眼不见为净吗?你太天真了。你亲手把我从笼子里放了出来。接下来,我要让你尝尝,
被猎物反噬的滋味。裴征毁灭计划第四步:切断所有退路,让他对我只剩下厌恶。完成。
五、致命的U盘出院那天,来接我的是裴征的助理,小陈。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,
戴着黑框眼镜,看起来很老实。他帮我收拾好东西,扶着我,一瘸一拐地走出医院。坐上车,
他递给我一个信封。“姜小姐,这是裴总让我给你的。”信封很厚。我打开,
里面是一张银行卡,和一把钥匙。“卡里有一千万。”小陈说,“是裴总给你的补偿。
公寓的地址也在里面。”一千万。买断我三年的青春,一张脸,一条腿。在裴征眼里,
我大概也就值这个价了。我把信封收好,没说话。车开到城西的公寓。房子不大,两室一厅,
装修得很简单。和我之前住的那个几百平的江景大平层,天差地别。小陈帮我把行李搬进去,
就准备走。“姜小姐,那我先回公司了。”“裴总说,以后……你们就不要再联系了。
”我叫住他。“陈助理。”他回过头,有点疑惑。我从包里拿出一个小小的U盘,递给他。
“这个,麻烦你帮我交给裴征。”“告诉他,这是我送他的,最后一份礼物。
”小陈犹豫了一下,还是接了过去。“好的,姜小姐。”他走了。我关上门,走到窗边。
这里是15楼,能看到大半个城市的夜景。很美。但我没心情欣赏。我在等。等一个电话。
我知道,裴征看到U盘里的东西后,一定会来找我。U盘里,是我这三年来,
收集的所有关于他和许安然的证据。有他们亲密的照片,有他们私会的视频。
还有……他为了给许安然家的公司行方便,动用关系,做的一些灰色交易的记录。这些东西,
任何一样曝光,都足够让裴氏集团的股价,发生一次大地震。我就是要让他知道,
我不是一个任人宰割的废物。我手里,有他的把柄。我要让他怕我。只有怕,
他才不会轻易丢掉我。只有怕,他才会把我重新拉回他身边。回到那个,离他心脏最近,
也最容易捅刀子的地方。果然,不到一个小时,我的手机就响了。是裴征。他的声音,
像是从冰窖里捞出来的。“姜谣,你什么意思?”我笑了。“没什么意思啊。
”“就是想让你看看,我这个废人,也不是什么都没做。”“裴征,你是不是以为,
我真的又蠢又瞎?”电话那头,是死一般的沉默。我能想象到他现在的表情。震惊,愤怒,
还有……一丝恐惧。“你想要什么?”他问,声音已经没有了刚才的盛气凌人。
“我不想怎么样。”我说。“我只是想提醒你,别把我逼急了。”“把我逼急了,
我什么都干得出来。”“比如,把这个U盘,匿名寄给几家媒体。”“你敢!”他低吼。
“你看我敢不敢。”我轻笑一声。“裴征,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。脸毁了,腿瘸了,
名声也没了。”“我一个烂人,光脚的不怕穿鞋的。”“倒是你,裴大总裁,家大业大,
应该比我更怕身败名裂吧?”电话那头,又是一阵沉默。良久,他才开口,声音里带着疲惫。
“……你到底想干什么?”“我想回到你身边。”我说,一字一句,清清楚楚。
“以前怎么样,现在还怎么样。”“你不是喜欢许安然吗?没关系,我不介意。
”“我只要裴太太这个位置。”“你疯了!”“是,我疯了。”我承认,“是你把我逼疯的。
”“裴征,我给你一天时间考虑。”“明天这个时候,我要么接到你的电话,
要么……这个U盘里的东西,就会出现在各大新闻网站的头条上。”说完,我直接挂了电话。
我靠在窗边,看着楼下车水马龙。心跳得很快。紧张,又兴奋。这是一场豪赌。赌注,
是我的后半生,和他的整个帝国。我知道,我赢的几率很大。因为我抓住了他的软肋。
他这个人,自负又爱面子。他绝不允许自己的人生,出现任何污点。第二天,我等了一整天。
手机,一次都没响过。我开始有点慌了。难道,我算错了?他宁愿身败名裂,
也不愿意再看到我?就在我快要绝望的时候,晚上十一点,门铃响了。我一瘸一拐地去开门。
门口站着的,是裴征。他看起来很憔悴,眼下有淡淡的黑眼圈。身上还带着酒气。他看着我,
眼神复杂得像一张网。“U盘的备份,都销毁。”他说,声音沙哑。“明天,
我带你去民政局。”我赢了。我看着他,露出了一个胜利的微笑。但眼泪,